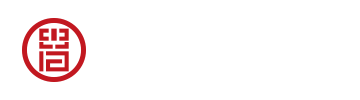差额补足承诺的理解与适用
中简律师|王天琪
在金融交易创新的背景下,在各类融资项目或者资产管理类项目中,债权人为保护自己债权的实现,除了设置常见的抵押、质押、保证等担保方式外,越来越多的出现差额补足承诺的增信措施,现拟针对差额补足承诺的相关问题予以探讨。
差额补足承诺的法律效力
一部分差额补足承诺是承诺人直接承诺在债务人未能按照约定支付应付本息的,由承诺人承担差额补足义务。由于差额补足承诺是承诺人与债权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且承诺内容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应当认定差额补足承诺具有法律效力。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认定差额补充承诺是否有效时通常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目前查询到的案例中法院鲜少否认这类差额补足承诺的法律效力。
但实践中也有部分所谓的“差额补足承诺”在条款设置上并非直接承诺在债务人未能按照约定支付应付本息的,由承诺人承担差额补足义务,而是使用其他措辞,如“尽最大努力督促债务人按期偿还债务”等表述,就不能达到在债务人未能如约支付本息时由承诺人来支付的效果。
差额补足承诺的法律性质
关于差额补足承诺的法律性质,目前争议较大,有观点认为差额补足承诺构成保证担保,也有观点认为差额补足承诺构成债务加入。
关于第一种观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六条规定:“本法所称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差额补足承诺与保证担保的相同点在于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或者承诺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但不同的是,保证担保作为一种担保方式,具有担保的从属性和补充性特征,而差额补足承诺相对于主债权债务具有独立性,是承诺人对债权人单独作出的承诺,因此差额补足承诺不同于保证担保。
对于此观点,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2017)最高法民终478号江苏省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合同纠纷案中,就差额补足承诺进行如下论述:“需要指出的是,《转让协议》约定由农行昆明分行承担的是特定资产收益权回购到期日之前的差额补充义务。上述义务属农行昆明分行作出的支付承诺,相对于被补充之债权具有独立性,农行昆明分行届期即应如数支付相应款项。此与通常具有从属性、补充性的保证担保不同,并不是在绿园置业公司不履行其回购义务时才由农行昆明分行向江苏信托公司依约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故其虽然具有增信担保的作用,但并非担保法意义上的保证担保行为。农行昆明分行上诉理由中主张《转让协议》‘名为转让实为担保’,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种观点,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一)》第十七条第规定:“债务加入是指第三人与债权人、债务人达成三方协议或第三人与债权人达成双方协议或第三人向债权人单方承诺由第三人履行债务人的债务,但同时不免除债务人履行义务的债务承担方式。”及第十九条的规定:“债权人请求第三人与债务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支持。当事人在合同中对责任形式有约定的除外。”由此可见,债务加入中的第三人与差额补足承诺中的承诺人虽然都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承担责任,但是债务加入中的第三人需要对全部或部分债务承担履行义务;而在差额补足承诺中承诺人承担的是差额补足义务,是当债务人无法履行全部债务时承诺人就差额部分承担的补足责任。因此差额补足承诺亦不同于债务加入。
因此,目前更多地把差额补足承诺视为不同于担保或债务加入的一种新型增信措施。法律性质的认定会对作出差额补足承诺的内部程序以及有效性的认定等产生影响。
总结
虽然目前对差额补足承诺性质的认定仍然存在一定争议,但在实践中差额补足承诺作为一种增信措施已被广泛应用,而且在发生争议时相当一部分差额补足承诺的效力也获得了法院的承认和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审判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法发[2017]22号)第二条第三款也表明要依法认定新类型担保的法律效力,除符合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外,应当依法认定新类型担保合同有效。但鉴于差额补足承诺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规定的担保措施,因此在具体适用时还需要结合其他抵押、质押、保证等其他担保方式共同作为交易的增信措施。
上一篇: GDPR框架下企业数据合规注意事项
下一篇: 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