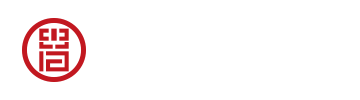股权代持案件裁判规则辨析
中简律师丨王天琪
股权代持伴随着投资主体的需求而产生,已经成为各类资本运作过程中的常见权益安排。对于股权代持法律效力的认定,目前主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规定,即如无《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则应当认定股权代持有效。
各个不同类型的公司在发生股权代持纠纷时如何对效力进行认定,我们可以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几个有关股权代持的案例来进一步了解实践中的司法裁判观点。
代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如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属于合同无效情形则有效
案情简介:贤源投资公司与黄南贲签订《代持协议》,约定黄南贲委托贤源投资公司作为对融炬小额贷款公司2400万元出资的名义持有人,翰廷投资公司以自己的名义在融炬小额贷款公司股东登记名册上具名。同日,贤源投资公司与黄南贲签订《补充协议》,对股权代持事宜进行了进一步的约定。后双方因股权代持事宜产生争议,黄南贲诉至法院请求解除《代持协议》及《补充协议》。
法院认为:“本院经审查认为,本案双方当事人均认可《股权代持协议书》及《补充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亦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故上述协议合法有效,并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实务要点:若股权代持协议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合同无效的情形,则根据《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一款的规定,该股权代持协议有效。
案例索引:(2017)最高法民申2851号
代持非上市股份公司股权:参照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
案情简介:海航集团与中商财富签订《委托投资入股代理协议》及《委托投资入股代理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海航集团自愿委托中商财富作为海航集团对营口沿海银行的出资入股代理人并代为行使相关股东权利,委托资金总额9360万元,其中7200万元用于出资入股营口沿海银行,委托期间,海航集团应向中商财富支付共计200万元的代为持股费用。后在中信济南分行与中商财富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对被执行人中商财富持有的营口沿海银行股份启动了司法拍卖程序,海航集团就上述执行标的提出案外人异议,要求法院确认海航集团为该股份的实际权利人。
法院认为:“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此进一步细化:‘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上述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虽是针对有限责任公司,但本案中营口沿海银行为非上市的股份公司,参照上述法律规定处理相关法律关系从性质上而言亦无不妥。”
实务要点:虽然《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针对的是有限责任公司,但是在法律法规对非上市的股份公司的股权代持未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的规定处理。
案例索引:(2016)最高法民再360号
代持上市公司股权: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
案情简介:杨金国与林金坤签订《委托投资协议书》与《协议书》,约定林金坤受杨金国委托,将杨金国以现金方式出资的人民币1200万元,以林金坤名义投资收购亚玛顿公司的股权,亚玛顿公司上市后双方共同分享收益。后亚玛顿公司正式在A股市场公开发行股票,杨金国请求林金坤名下1200万股亚玛顿公司股份及相应的红利为其所有并将股票过户至杨金国名下。
法院认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授权对证券行业进行监督管理,是为保护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要求拟上市公司股权必须清晰,约束上市公司不得隐名代持股权,系对上市公司监管的基本要求,否则如上市公司真实股东都不清晰的话,其他对于上市公司系列信息披露要求、关联交易审查、高管人员任职回避等等监管举措必然落空,必然损害到广大非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从而损害到资本市场基本交易秩序与基本交易安全,损害到金融安全与社会稳定,从而损害到社会公共利益。”“故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等规定,本案上述诉争协议应认定为无效。”
实务要点:在有限责任公司及非上市的股份公司中,股权代持的影响主要存在于代持双方及其他股东之间,并不会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影响;但是由于上市公司的公众性,如存在股权代持可能会损害不特定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同时上市公司的股权代持直接违反了相关金融监管措施的规定,违背了证券市场的公共秩序,因此最高人民法院认定此类股权代持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4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而无效。
案例索引:(2017)最高法民申2454号
代持保险公司股权:因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效
案情简介:天策公司与伟杰公司签订《信托持股协议》,协议约定:鉴于委托人天策公司拥有正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2亿股的股份(占20%)的实益权利,现通过信托的方式委托受托人伟杰公司持股。受托人伟杰公司同意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后天策公司要求伟杰公司依据《信托持股协议》终止信托,将信托股份过户到天策公司名下,并结清天策公司与伟杰公司之间的信托报酬。
法院认为:“天策公司、伟杰公司签订的《信托持股协议》内容,明显违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八条关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保险公司的股权’的规定。”“违反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有关禁止代持保险公司股权规定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直接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一样的法律后果,同时还将出现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损害包括众多保险法律关系主体在内的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后果。”“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等规定,本案天策公司、伟杰公司之间签订的《信托持股协议》应认定为无效。”
实务要点:与前述对上市公司的裁判思路类似,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代持保险公司股权会加大保险公司的经营风险,不利于保持保险公司经营的稳定性,不利于保护投资者和众多不特定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这种潜在的风险会危及金融秩序的正当性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因此认定此类股权代持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4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而无效。
案例索引:(2017)最高法民终529号
股权代持协议无效情况下因代持行为产生的投资收益及股东身份如何认定
(一)关于投资收益
法律规定:《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二款:“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在杨金国、林金坤股权转让纠纷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中双方协议因涉及上市公司隐名持股而无效,但这并不意味着否认杨金国与林金坤之间委托投资关系的效力,更不意味着否认双方之间委托投资的事实。”“据此,因本案双方协议虽认定为无效,但属于‘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情形,故杨金国要求将诉争股权过户至其名下的请求难以支持,但杨金国可依进一步查明事实所对应的股权数量请求公平分割相关委托投资利益。”
由此可见,股权代持中包含了股权归属关系与委托投资关系,在股权代持协议被认定无效的情况下,无效的法律后果是对于关于股东身份和权利的约定无效,但隐名股东基于委托投资而形成的财产权益并不因此而无效,根据公平原则,隐名股东仍可以请求分割委托投资利益。
(二)关于股东身份
法律规定:《公司法解释三》第24条第三款:“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在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海航集团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代持情况下,即名义股东与实际股东分离时,通过合同法规制解决。即使海航集团为涉案股份的实际出资人,也并不当然地取得营口沿海银行的股东地位。”
代持法律关系其本质属于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受合同法相对性原则的约束,隐名股东就该债权仅得以向名义股东主张,对合同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不产生效力。代持情形下,隐名股东的财产利益是通过合同由名义股东向实际股东转移,需经过合同请求而取得,若隐名股东请求成为公司股东,则需经过半数股东同意,其并非当然取得股东地位。